写小说,是人物角色的创造,但功夫深了,作家带入了角色,走不出来,最终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小说里的角色,而且现实生活其实变成了小说。诺曼梅勒说:我常常觉得,我自己其实是诺曼的秘书,要见诺曼本人吗?先见我好了
有一派心理学认为,男人的初恋决定他一生的情感定位。辛荑小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,女孩父母的单位出产白布,小女孩只穿白布衣服。我可以想象,那时候,在灰头土脸的北京市,在灰头土脸的人群中,那是怎样的视觉效果。长大了的辛荑看见白大衣,就会阴茎充血,龟头上昂。 冯唐 《万物生长》1
冯唐 《万物生长》1
 冯唐 《万物生长》1
冯唐 《万物生长》1群体感情的狂暴,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,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。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——而且人数越多,这一点就越是肯定——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,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。在群体中间,傻瓜、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,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,会感觉到一种残忍、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。 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 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幻觉—自从出现文明以来,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。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,设立祭坛,超过了所有其他人。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,这些牢不可破至高无上的力量,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。毫无疑问,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,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,确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。假如谬论对人们有诱惑力,人们更愿意崇拜谬论,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,也可以很容易的成为他们的主人,凡是让他们幻灭的,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。 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 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人们经常说起那家大众剧院,它只演令人压抑的戏剧,散场后,必须保护扮演叛徒的演员,免得他遭到观众的暴打。他所犯的罪行,当然是想象出来的,引起了群众的巨大愤怒。我觉得这是群体精神状态最显著的表现之一,这清楚地说明,要给他们什么暗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。对他们来说,假与真几乎同样奏效。他们明显地表现出真假不分的倾向。 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 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被爱应该是件高兴的事,可慢慢的觉得,这已成了一种负担。 山本文绪 《蓝另一种蓝》1
山本文绪 《蓝另一种蓝》1
 山本文绪 《蓝另一种蓝》1
山本文绪 《蓝另一种蓝》1




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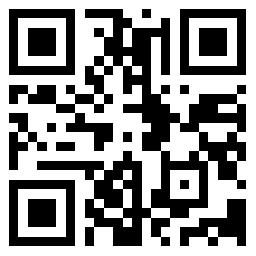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