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我的这副杰作拿给大人看,我问他们我的画是不是叫他们害怕。他们回答我说:“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?”我画的不是帽子,是一条巨蟒在消化着一头大象。于是我又把巨蟒肚子里的情况画了出来,以便让大人们能够看懂。这些大人总是需要解释。 安托万·德·圣-埃克苏佩里 《小王子》1
安托万·德·圣-埃克苏佩里 《小王子》1
 安托万·德·圣-埃克苏佩里 《小王子》1
安托万·德·圣-埃克苏佩里 《小王子》1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,和国人不想干,无从受害。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,虽曰国人,要借以泄愤的时候,只要给予一种特异的名称,即可放心剚刃。先前则有异端、妖人、奸党、逆徒等类名目,现在就可用国贼、汉奸、二毛子、洋狗或洋奴。 鲁迅 《鲁迅杂文精选》1
鲁迅 《鲁迅杂文精选》1
 鲁迅 《鲁迅杂文精选》1
鲁迅 《鲁迅杂文精选》1如果脑残会飞的话,这里简直就是飞机场嘛 汪远 《爱情公寓》2
汪远 《爱情公寓》2
 汪远 《爱情公寓》2
汪远 《爱情公寓》2国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常见病,那就是习惯于作“逆向扮演”。他们把古代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涡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机巧层面,往往用极端的方式扮演各种角色,又轻易地滑到另一极端,还是在扮演。例如,不少沉溺“国学”极深的人,可以在国运危殆之时轻易弃“国”,成为汉奸,像罗振玉、郑孝胥、周作人、梁鸿志、胡兰成等等都是如此。后来,那些在极左时期制造灾难的文人,转眼也会变成追查灾难的“斗士”,两头都扮演得慷慨激昂。直到今天,不少在传媒上最具攻击性的文人仍然喜欢“逆向扮演”,完全不在乎言行不一、内外分裂、前后矛盾。 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 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




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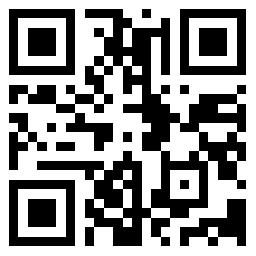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