耻感文化基本上是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维护善行。罪感文化则通过内心的罪恶感来维护善行。前者的羞耻感产生也往往源自外部,是一种针对别人批评的反应,或者因为被大众讥笑、排斥,或者是他自己觉得受到了讥笑,但无论哪一种,这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强制力。
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章第一句:“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”按正宗的解释,就是“能说得很明白的‘道’就不是‘大道’”。但换个角度,那时没有句读,所以可以有另外一种句读方式:“道可,道非,常道;名可,名非,常名。” 白岩松 《白说》1
白岩松 《白说》1
 白岩松 《白说》1
白岩松 《白说》1一个人面对一种宏大的文化,就像一个小孩面对一座大山。尽管住在山脚下,天天看见它,但要真正了解它,几乎不可能。这是因为,它的悠久历史,与小孩的年岁构不成平等的对话;它的惊人体量,与小孩的躯体形不成合理的互视。 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 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总是在互动中发展着,并朝着相互交叉和融合的方向演进,以致融为一体,形成崭新的精神文化。在这一过程中,物理学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,有助于激发人类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创造更为美好的物质生活。 陈佳洱 《佚名》0
陈佳洱 《佚名》0
 陈佳洱 《佚名》0
陈佳洱 《佚名》0






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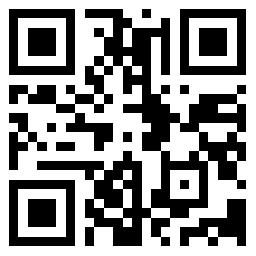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