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都是平等的,人人都有两个自我,一个是病态的,一个是健康的;一个走向生存,一个走向死亡。我们每一个人,其实都足以代表整个人类。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中,都拥有向往神性的本能,都有达到完美境界的欲望;而在每个人的身体中,同样都有懒惰的原罪。无所不在的熵的力量,试图把我们推回到人类进化的初期——那里有我们的幼年,有母亲的子宫,还有荒凉的原始沼泽。
他已经揭开了曾遮蔽它们的那道幕,但是要把它们这么多年的帷幕重新拉回去并不那么容易。这当中有朋友的面孔,也有敌人的面孔;也有从人群中贸然出现、几乎已成为陌生人的许多面孔;有许多已变成老太太的年轻的、容光焕发的姑娘的面孔;还有被坟墓覆盖、已变了样的面孔,但超越死亡力量的记忆仍然将它们以昔日的青春和美貌乔装打扮着,只是炯炯有神的目光、灿烂的微笑、灵魂透过肉体的假面具笑逐颜开,以及死亡之外美妙的窃窃私语,它们虽为死亡所改变却得以升华,离开人间只是为了提供一盏发出柔和光辉的灯,照亮了通往天国之路。 狄更斯 《雾都孤儿》1
狄更斯 《雾都孤儿》1
 狄更斯 《雾都孤儿》1
狄更斯 《雾都孤儿》1我向往有一天能躺在云峦那柔柔的曲线里睡一个宁静的午觉。这说来可笑,但我无法禁止自己在看到云朵时不兴起这样的念头。于是,望天的脸庞虽是充满喜悦与笑容,望云的眼神,则是永远不见答案的天问。 简媜 《水问》0
简媜 《水问》0
 简媜 《水问》0
简媜 《水问》0我在半梦将醒的时候,很认真地把这个梦继续下去。即便在迷糊中,我也知晓这是生命的格律,等待一些我无法掌握,甚至完全了解不了的,但是明知即将发生的事。而时光如此出色,大地必将完美安排。 乔阳 《在雪山和雪山之间》0
乔阳 《在雪山和雪山之间》0
 乔阳 《在雪山和雪山之间》0
乔阳 《在雪山和雪山之间》0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,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。 廖一梅 《柔软》0
廖一梅 《柔软》0
 廖一梅 《柔软》0
廖一梅 《柔软》0满向往,但更多的是畏怯。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,没有先例供我遵循,就连签证都非常棘手。 然而,几乎没有太多犹豫,我上路了。2011年深秋,我第一次抵达 塔什干,立刻就被中亚的“呼愁”吸引。接下来的几年里,我开始 持续探索这片土地。九年倏忽而逝,我几乎去到了我在中亚可以去 到的所有地方。我看着自己当年的冲动渐渐变成了一张真实的履历, 张标满记号的地图。 与此同时,我的人生也在悄然变化:我辞去工作,成为作家。我像游牧者一样,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,用自己的方式旅行 日复一日地写作。原先不知如何面对的问题,渐渐有了答案,渐渐变得清晰。 如今,我在中亚的旅行终于接近尾声。我来到阿拉木图汽车站,准备搭车前往扎尔肯特,从霍尔果斯口岸回国。 刘子超 《失落的卫星》0
刘子超 《失落的卫星》0
 刘子超 《失落的卫星》0
刘子超 《失落的卫星》0以前我曾今感受过一个人死亡或离去对于活着和留下的人的意味,我觉得那是一片空虚,生活很快会把它填满。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,绝不是一个数量概念。失去一个曾今存在过的人,意味着失去全部。 徐晓 《半生为人》0
徐晓 《半生为人》0
 徐晓 《半生为人》0
徐晓 《半生为人》0譬如一个武士,用全副重铠披戴起来,他势必找一敌人来决斗一番,否则便将此全副披戴脱卸,再否则他将感到坐立不安,食不知味,寝不入梦,老披戴着这一副武装,势必病狂而死。目前的世界,几乎对外尽在找敌人厮杀,对内又尽在努力求脱卸此一身重铠,同时亦尽在坐立不宁寝食不遑的心情中走向病狂之路。但我们须知,正因其是一武士,所以能披戴上这一副重铠。并不是披戴上了这一副重铠,而遂始成其为武士的。而没有披戴上这一副重铠的人,却因于惧怕那武士之威力,而急求也同样寻一副重铠披戴上,而他本身又是一羸夫,则其坐立不宁寝食不遑将更甚。其走向病狂之路将更速。若使遇到一敌人厮杀,其仍归于同一的死亡绝命,也就不问可知了。 钱穆 《湖上闲思录》0
钱穆 《湖上闲思录》0
 钱穆 《湖上闲思录》0
钱穆 《湖上闲思录》0


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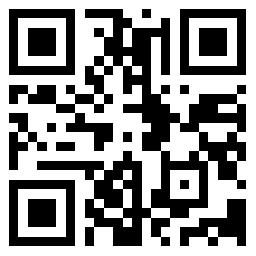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