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文章的人应该从创作的乐趣、舒解纷扰烦乱的文思中寻求成就感,同时要对其他所有事无动于衷,不去在乎自己作品的成败毁誉。
记得王尔德说过,“艺术并不模仿人生,只有人生模仿艺术。” 张爱玲 《重访边城》1
张爱玲 《重访边城》1
 张爱玲 《重访边城》1
张爱玲 《重访边城》1话须通俗方传远,语必关情始动人 冯梦龙 《警世通言》2
冯梦龙 《警世通言》2
 冯梦龙 《警世通言》2
冯梦龙 《警世通言》2公元六七二年冬天,一篇由唐太宗亲自写序,由唐高宗撰记的《圣教序》刻石。唐太宗自己的书法很好,但刻石用字,全由怀仁和尚一个个地从王羲之遗墨中去找、去选、去集。皇权对文化谦逊到这个地步,让人感动。但细细一想,又觉正常。这正像唐代之后的文化智者只敢吟咏唐诗,却不敢大言赶超唐诗。 同样,全世界的文化智者都不会大言赶超古希腊的哲学、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、莎士比亚的戏剧。 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 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
余秋雨 《中国文脉》1优质的稠密的不完美性能够刺激人的意识,唤起注意力。如果听舍此无他那样的完美音乐和完美演奏开车,说不定就想闭上眼睛一死了之。而我倾听《D大调奏鸣曲》,从中听出人之活动的局限,得知某种完美性只能通过无数不完美的聚集方能具体表现出来,这点给我以鼓励。 村上春树 《海边的卡夫卡》1
村上春树 《海边的卡夫卡》1
 村上春树 《海边的卡夫卡》1
村上春树 《海边的卡夫卡》1说不定作家在创作恶棍时,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天性,因为在文明社会中,风俗礼仪迫使这种天性隐匿到潜意识的最隐秘底层下;给予他虚构的人物以血肉之躯,也就是使自己那一部分被压抑的自我得到舒展。从而满足来自本能的自由快感。 毛姆 《月亮和六便士》1
毛姆 《月亮和六便士》1
 毛姆 《月亮和六便士》1
毛姆 《月亮和六便士》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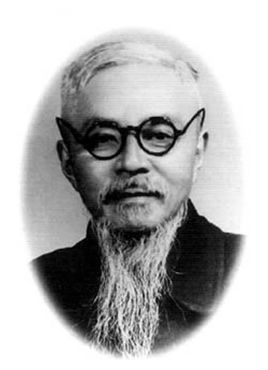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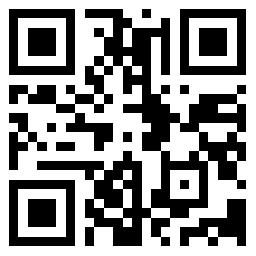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